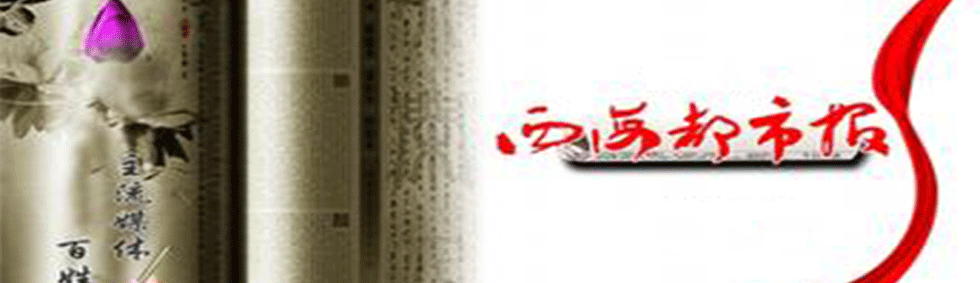
河湟婚俗.娶亲——
远方移花人,来移金银花
文/王祥奎
河湟谷地汉族先民大多在汉唐时期从中原迁徙至此,伴随着农耕文化的西移,便形成了牧业文化和农耕文化相融合的多元河湟文化,包括独具特色而又异彩纷呈的婚俗文化,且封建社会的等婚姻礼俗也在河湟流域得以传承。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河湟谷地仍然保留着诸如请媒人、合婚、订婚、送彩礼、添箱、娶亲等规程礼仪。
娶亲妨忌及夜间娶亲的来历
说起娶亲,就是把新人从娘家娶到婆家。在河湟谷地,娶亲的人数必须包括在内成双数,或六人或八人不等,寓意是成双成对大吉大利。娶亲人中还必须安排一名懂礼节及能说会道的领头人,若遇到女方家出难题,就能善于应付,巧于化解。同时,娶亲队伍中不能有妨忌的人,妨忌,就是有碍于婚姻的人,选定娶亲人员时,要考虑属相、身体健全情况(主要指不全换的半边人)及是否戴孝等诸多因素,因河湟谷地娶亲特别害怕冲了“喜”。此外,为了婚事及婚后的和顺,还会考虑到猪狗牛羊等家畜。在新人上轿到娘家人恭喜冠戴前,婆家要将这些家畜圈起来或寄养到别家,不许放出,以防惊叫。人们认为属相克者、寡妇、孕妇或半边人等冲了喜事,新婚夫妇的感情会遭受磨难,挫受波折。同时,娶亲的人中还必须有娶亲奶奶,而娶亲奶奶一般是婶子、或嫂子,因河湟民间“姑不迎,姨不送”的讲究。
在河湟谷地,娶亲都在拂晓之时。说起来还特别有讲究。因为河湟民众认为“青龙头上入洞房,金玉满堂后代昌。”而青龙是中国古代的“东方之神”,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的角星与亢星,在十二宫中分布在子时后、寅时前。这个时间恰是凌晨拂晓前,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青龙头上”的时辰,也是新人入洞房前最理想的时刻。这个习俗史料也有记载。譬如,《酉阳杂俎》记载: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阴来也。今行礼于晓。《礼仪.士昏礼》也记载:昏礼下达。同时,这种习俗也与抢婚有着一定的渊源。
据老人讲,在古时,有着大量的抢婚、抢亲之现象。据考证,《诗经》中的“薪”是一种上古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婚姻形态——抢婚,“薪”也就是上古抢婚中的一种照明用具、攻防武器。在冷兵器时代,就有“人马逼近,刀不如棒”的说法。譬如,《唐风.绸缪》记载: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周南.汉广》记载: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从中可以看出,掠婚之风商周间未犹绝也。”《诗经》产生的时代,抢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
娶亲问答词
每当子夜寅时前,娶亲人如期来到新人娘家门口,点火、鸣炮。之后,领头人便去叫门,只听门内一阵阵笑声与嘈杂,于是乎,门内外便开始了一场婚俗文化的论战——
“金锁银锁开门来。”
“门外是何人?叫门做什么?”
“远方移花人,来移金银花。”
“你是移花人,脚蹬什么靴,身穿什么袍,头戴什么帽,怀里揣的啥,手里拿的啥?”
“我足蹬翰林靴,身穿紫薇袍,头戴龙凤盔,怀揣聚宝盆,手提荣华富贵,仙泉圣水,怀抱着金盏银盆来移花……”
“拿钥匙来。”
随后,娶亲人就将红包塞进门缝。“你的钥匙太小,开不开!”娶亲的人又塞进一个红包,“钥匙还是太小,开不开!”“慢慢来,别着急,锁子合适才能打开门。”娶亲人再塞红包,如此反复多次,将准备的十多个红包尽数塞进门缝。
“锁子开了,恭请远方的贵客进门!”此时,娘家人方将大门打开,热情地迎接娶亲人进门。进门后,娶亲奶奶将带来的衣物等物牢牢抱在怀里,以防娘家人抢夺。因为,在河湟婚俗中有一种以图热闹或讨吉利的“偷、抢”文化。这种“偷、抢”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抢偷,而是彰显河湟婚俗文化规程的繁杂。如果娶亲礼物被娘家人夺取或“偷”取一样,男方就得以高价赎回。
待娶亲人就坐后,娘家的大东一一递烟,并倒上放有红枣的“空茶”。喝过“空茶”,娶亲奶奶与领头人向送亲奶奶交付娶亲的衣物、化妆品等。此仪式在娶亲中颇为隆重,送亲奶奶也格外认真负责,而且女方家的女客诸如婶婶、娘娘、舅母等也会故意“刁难”男方,论长道短。这道规矩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刁难,而寓意是把不吉利不和顺的的事儿说得烟消云散。但有时不满因男方家吝啬心存刁难之意,遇到这种现象娶亲人格外大度,百般忍耐,尽量打圆场以求圆满。
哭嫁歌与劝嫁歌
在河湟的婚礼习俗中,有哭嫁歌、劝嫁歌、迎宾歌、拜堂歌、禳床歌等诸多文化元素,而哭嫁歌与劝嫁歌属于封建社会的产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哭嫁歌与劝嫁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被岁月的浪潮湮灭在历史的车辙里。但从老者的讲述中真切感受到河湟婚礼歌的独具特色,尤其是哭嫁歌、劝嫁歌是真正属于“动之以情而发之于声”的一种独特文化。即将出阁为婆家新媳妇的女儿,在诸多亲眷的宽慰声里,话别语中,早已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带春雨”了,有些姑娘还用哀吟悲唱来“说尽心中无限事”——
“自幼跟着父母转,未曾离开半月天,如今我把父母抛,怎不叫女儿费煎熬;我姊妹兄弟相爱惜,一搭儿相处多少年,一年三百六天,时时刻刻摩着肩,姊妹兄弟情不浅,如今我要成孤雁……”
“听见门外鞭炮响,女儿心头阵阵痛,闺蜜姐妹俱流泪,陪我流泪湿衣襟。我把爹妈叫三声,女儿心上有大痛……”
看着自己的爱女泪挂香腮,女方家的长辈女性用款款语言,唱着劝嫁歌,敲开女儿凝结在女儿心头的磊块,且晓之以理地传授为人妻的做人之理——
“玉杯水酒双手上,手巾搭在盒儿上。姐儿啊!你双膝往前跪,句句话儿听明白。你明日早上上花轿,高茶贵饭孝公婆,扫地嫑叫尘土扬……”
……
等娶亲的衣物、化妆品等东西交付完毕,送亲奶奶将这些衣物在水缸上或水盆上抡一抡,才给新娘穿戴上轿。其寓意为把一路上的不干不净、路神野鬼、半边人用清水洗净冲散。
在亲人的送行中,新郎背着蒙着红色盖头的新娘走出娘家门,在出门之际,新娘将一把红筷子撒向身后……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进入二十一世纪,河湟婚俗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混融、多姿多彩的风貌,虽然有传统的内容,但大都只留其仪式的象征意味。岁月悠悠,传统的河湟婚俗成为我心头淡淡的乡愁,并在淡淡的乡愁里走向中年。
——
王祥奎,青海互助人,现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苑散文网签约作家,中国乡趣网通讯员,数十篇人物通讯及新闻报道、散文诗词发表于《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西海都市报》等报刊杂志,多篇散文在省内外征文比赛中获奖。现供职于西宁市教育系统。青海在线文化传媒签约作者。
==============================
青海在线文化传媒出品。原创作品,请勿转载。《青海读书》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ngxingxing.net/xhdsbzn/101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