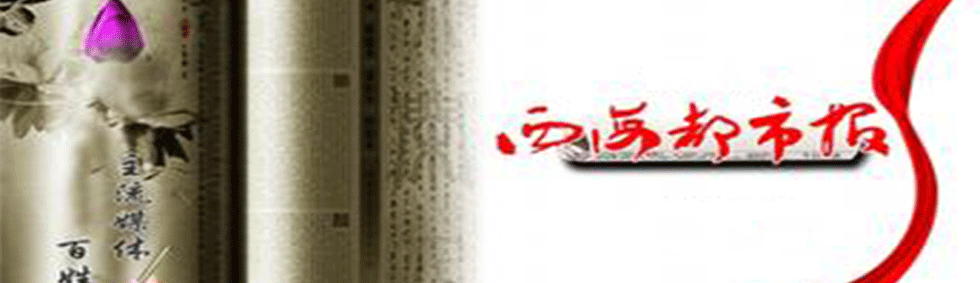
编者按:近日,由省体育局等四个省区的相关部门共同发起雪豹、藏牦牛、藏羚羊将为北京年冬奥会吉祥物的倡议,并就为申报冬奥会吉祥物进行推介、宣传。果洛州文体广电局年5月在《西海都市报》开设专栏,以八个正版的版面重点对藏牦牛进行了专题宣传介绍,为藏牦牛入选北京年冬奥会吉祥物开展了集中宣传、推介。专栏文章并在多家报刊和网络媒体刊发和转载,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形成了一定的宣传基础,打造了一定的宣传声势。
今将该专栏文章,集中编发,分享于此,以飨读者!
巡游人间的“星辰”——牦牛记之五中国已有三千年以上的牦牛驯养历史。世界上现有牦牛大约万头,85%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省区。剩下的15%,分别分布于蒙古国,中亚地区和俄罗斯的高地。
作为青藏高原最大的哺乳动物,牦牛的驯化和放养,主要由高原游牧民族完成。范晔的《后汉书》中写道:“冉駹夷出旄牛,重千斤,毛可为旌,观此则牦牛之名盖取诸此。”这是古人作出的推测。实际上,如果深入藏文化的丰富世界,我们才可能感受到牦牛在藏民族文化心理的多义性和主要象征,才能理解牦牛和藏民族的精神信仰、生活实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牦牛这一年轻而又古老的动物,是藏民族先民最早驯化的牲畜之一。从这个驯化过程,也能窥测藏民族文化心理的成长史,生产和物质的发展史。因此,在藏族的神话传说故事中,牦牛的涵义极为丰富。
有一则关于牦牛的传说是这样的:一个名叫色安布的小伙子,从一只小鸟处收到山神儿子带来的信。信中说,山神要把女儿嫁给他。小伙子很高兴地答允了这门亲事。山神把大女儿变成一头猛狮,色安布见了很害怕;山神把二女儿变成了一条蛇,色安布望而却步。山神把小女儿变成了一头野牦牛,并向他猛攻。色安布沉着地用神赐的魔棍一点,野牦牛变成了一个姑娘。色安布与姑娘成亲生子,生活在一起。很久之后,姑娘上天去了,她留下的唯一的儿子,成为了藏族塔拉克氏族的祖先。
这是一则文化寓意相当深厚的民间故事,其中暗含藏族对于自然的认识,隐喻着藏族先民的牦牛驯化史,以及与牦牛建立的亲人般的共生关系。把自己的族源和牦牛联系起来,不仅仅因为牦牛是藏族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而且,牧人从牦牛那里获取了一种相符于雪域高天的审美观、生活观和精神支撑。
藏族史书《西藏王统记》中,也有类似的神话记载:止贡赞普与大臣罗旺达孜决斗,罗旺达孜用计杀死赞普,夺了王位,并命止贡赞普的王妃牧马。王妃在山上放牧时梦见与雅拉香波山神变幻的一位白人结合。醒来只见一头白牦牛从身边走开。这位王妃妊娠后生下一个血团。她把血团放在一只野牛角里,孵出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如列吉意即,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从角中出生的人。
从以上两则传说中,可以看到藏族对于牦牛强烈的情感认同。藏族的山水崇拜,尤其是神山的化身,更是明白地显示了这个伟大民族对于牦牛护持的感恩之情。从西藏到青海甘肃,再到四川云南,青藏高原如列如队的高峰巨峦,组成了地球上的高海拔俱乐部,其山神漫步云际,穿行人间,敦守四野,成为了一方民众心理的依靠。有意思的是,雅拉香波、冈底斯、念青唐古拉、阿尼玛卿、年保玉则等著名的山神,他们的化身都是白色的牦牛。将神圣、崇高、纯净、吉祥的白色,和生产生活中的伴侣牦牛结合起来,藏族就这样发明了一个通联神界与凡间,力量与审美高度融合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象征既具有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又带有青藏高原显著的特征,在今天仍然值得深深品咂。
像大地一样坚实的牦牛,带来安康生活的吉祥的牦牛,教会人们发现美的结构的牦牛,当得起各种礼赞。但是,思维能力强大、逻辑推导严密的藏族,不是单一地看待主观和客观世界,对于牦牛的认识和表达,附着着藏族的发展记忆和对艰辛生活的根本认识。牦牛的凶猛和蛮力,应该给几千年前的驯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后世对于牦牛的另一种表述。比如说,那则关于朗达玛的传说中就含着对于牦牛之猛力的暗写。那则传说如下:有兄弟三人在祈祷时只为自己,而忘记了向佛祖推荐牛,牛知此事后,发誓来生要毁灭佛法,即转生为达玛赞普,头上长出两个骨突,状若牛角,形象凶恶。在长篇巨型史诗《格萨尔》中,则将牦牛描述为力大无比的神:北方魔国魔王的寄魂红铜角野牛被岭地人们煨桑时燃起的桑烟所激怒,先后冲入聚集的霍尔和岭地人马中间,造成了人畜大量伤亡。在史诗中,野牦牛具有撼天动地的力量,它的出现带着风暴、日蚀、野火等等可怕灾难的能量。
采取两分法,辨证地认识和理解牦牛,认识我们身在其间的天地和事物,显示藏族精准的观察力和思想力。这样的认识完整清晰,价值取向却又褒贬有度。野牦牛的力量和凶悍,被民众充分利用,成为了镇宅护守,家庭和财产的保护神。当年,可可西里盗猎猖獗之时,索南达杰等人组成的野牦牛队成为那片净土生灵的守卫者,成为了藏羚羊的保卫队,其功勋永勒江源。
虽然,人们惊惧于自然(牦牛)原始的伟力,但是,对于自然(牦牛)的赐予更是感恩礼赞。在藏族神话中,人们把野牦牛称作天上的“星辰”,古老的藏歌中时常出现神牦牛巡游人间的奇境。神牛和后来传入的佛教结合,使得白牦牛的地位上升。据说,莲花生大师初到藏地降伏白牦牛,并让白牦牛神成为了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对于白牦牛的崇拜和礼赞,千百年来贯彻在藏家儿女的生活里。就在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牧民才旦和儿子两代人经过了30年的努力,建立了自家多头白牦牛核心种群。天祝白牦牛是海拔米以上高寒草原上的特有畜种,是稀有的珍贵遗传。最有力的文化传承和生物生态保护,来自人们自觉的认识和自觉的行动。天祝白牦牛的保护,就是这样成功的案例之一。
游牧高大陆——牦牛记之六金丝牦牛、白牦牛固然珍稀,但是和藏家儿女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只能是黑牦牛和杂色牦牛。让最普遍的事物,成为世界的支撑,这可能是造物的智慧。普通的黑牦牛和杂色的牦牛,负载牧民的希望,负载着一个个部族的兴衰。
在漫长的游牧放养史中,藏族和牦牛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藏族的创世神话讲述万物起源时,将重要事物都归总于牦牛:“牛的头、眼、肠、毛、蹄、心脏等均变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森林山川等等……”安多地区流传的神话故事《斯巴宰牛歌》应和了以上创世神话:“斯巴最初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斯巴宰小牛时,砍下牛头扔地上,就有了高高的山峰;剥下牛皮铺地上,便有了平坦的原野……”斯巴的意思是“宇宙”“世界”,这就是说,世界的主要物质是牦牛构造的。
牦牛首先是世界的基础,然后随着驯化史和牧人一起顶着浓稠的大雾,从古代走向今天,从一处草场走向另一处草场,和人类共同创造了一种高原文明。《后汉书·西羌传》中写到河湟羌人时说:“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其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
从雅隆河谷最早出现的“六牦牛部”,到牦牛羌,再到牦牛郡、牦牛县、牦牛河、牦牛沟、牦牛山、牦牛谷,把青藏高原称为牦牛的世界不是夸张之词。高原先民和牦牛在这片高大陆同生共长,成为了文明的象征。从《后汉书·西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河湟羌人已经开始驯养和放牧牦牛了。至公元年,吐谷浑人进入青海海南、海北、海西和柴达木盆地,继续驯化放养昆仑山、祁连山地区的野牦牛,牛群仍然是他们生活和经济的主要资源之一。一句话,游牧高原,牦牛和羊群、马匹、护犬,都是部族和牧民家的标配。在夏季,当旅游者拿起手机或者相机,在高山草甸或者湖边草原,把黑宝石一样灿烂的牦牛群摄入镜头时,可能很难意识到这种在《山海经》中描述为:“潘侯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生毛,名曰牦牛”的动物,其实是高原的象征,是高原文明的基石,也是高原人家的一员。
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脆弱的植被生态,莫不对游牧提出了严峻的试题。逐水草而居的大范围游牧,半定居的小范围游牧和季节性游牧,是藏族牧民采用的三种最基本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所蕴含的艰辛都非外人可以完全感受和认识的。
以长江源头和黄河源头的广大区域为例,这一带草场辽阔,物种繁多。然而,因为冰冻期长,风沙大,草场返青晚,所以,牧草不丰,载畜量有限。在这里游牧的牧民一年四季频繁搬家,以求取牛羊可以生息之地。千辛万苦找到的牧场,居住时间最多却不能超过两个月,短则五到十天就得搬家。生存环境就是这样考验人的承受力。
藏历二、三月间,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都还大雪纷飞,气温极低。这里的牧人们却只能告别日渐荒芜的冬季牧场,从唐古拉以北向唐古拉以南的夏季牧场迁徙。黝黑的脸,皲裂的手,老人蹒跚的脚步,婴儿的啼哭,灶膛的火焰,残剩的奶茶,正在被虔教收起的佛像……所有的一切,都被编织在迁徙的长旅中。成年男子和他们的妻子是这个行旅的指挥和主要实施人,而牦牛则是这支队伍物资的负载者。一头牦牛的寿数大约是15年至20年。牦牛长到四岁即可以负重,几百斤重的东西压在这个沉默生灵的肩背,听着它们的咀嚼声和喘息声,人和羊群才踏踏实实地走向前方。
一般牧人全家的物品,大约有10头牦牛就可以驮完;富裕的人家可能需要二三十头。在风雪吹得人畜睁不开眼睛的山垭,山腰和山岗;只有排在羊群前面的牦牛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地踩踏着大地,驮在它们身上的一些货品间或发出碰撞的声音;那沉闷或者响亮的声音仿佛都是种鼓舞,给予牧人极大的心理支援。
这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牦牛被称之为高原之舟。牦牛坚实的犄角,硕大的头颅,厚重的躯体,沉稳的步伐,从风雪中浮现出来,恰似一艘艘舰船从迷雾横锁的江河中沉静驶出。
三月草发芽,四月黄杂绿。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无论是对采取哪种方式游牧的人们来说,都是饥馑的时刻。为了躲避大雪、大风和降温,牧人要审时度势,规划迁徙路线;尽管如此,有些灾难仍然不可避免。在迁徙途中,遇到人畜难以通过的风雪地区,往往是负重的牦牛排在人和羊群之外,以厚厚的长毛和敦厚的躯体抵御风雪。我读过有关报道,有牧人迁徙时遇到暴雪,被困很长时间后终得救。牧人之所以能挺到救援时刻,就是因为外围的牦牛即使已经冻僵,也仍然挺立着护持里面的人和羊群。
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曾说:人类应该向苦难学习。何止是该向苦难学习,我们还应该看看身边这些面对苦难的生灵,在它们身上流露着一种来自洪荒时代的天真和勇敢,智慧和责任。牦牛就是这样的吉祥灵兽。
青海,世界牦牛之都——牦牛记之七
游牧、转场、迁徙,牧人就是在这样的行动中了解气候地理,认识霜天万类,定位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首先来自生存的需求。
羊群和牛群是牧人在这高寒大陆的生活保障。耐寒怕热、体形庞大的牦牛,给牧人在衣食住行多层面提供了保障。
牧民的家是驮在牛背上的。无论游牧到什么地方,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支撑帐篷的木桩砸入地下,把四角的牛毛绳子系紧,然后在帐篷中穿入一梁,以两根立柱支在梁下。这样,一座牧人的住房就像蘑菇一样顶立在草地上。
需要说明的是,帐篷大都是由牛毛织就的。一头公牦牛每年可剪毛一次,抓绒一两次,一年可以剪两三斤毛。牛毛密实厚重,是遮风挡雨的好材料。在今天,尽管那种追风逐月、寻觅水草的游牧生活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黑牦牛帐房仍然留存在藏族牧人的记忆里。有歌词唱道:“走过的帐房都忘了/唯有姑娘的黑帐篷忘不了/忘不了……”牦牛帐篷伴随藏家儿女生活了千百年,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实用功能,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符号。
这种情感记忆,被青海玉树人放大了。年,索才制作了三顶0多平方米的大型牛毛帐篷,每顶价值万元左右。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在玉树巴塘草原经过测量,显示其中一顶牦牛黑帐篷单体总面积为.08平方米,被认定为“世界最大牦牛黑帐篷”。据悉,这顶帐篷将在年青洽会上亮相。
温暖的家来自牦牛的赐予,饮食一样离不开牦牛滋养。牛奶以及由牛奶所制作的酸奶、酥油、奶渣,都是牧人的主要食物。每年五六七三个月,是高原草场最为丰美的时节,天空明净,空气清新,碧水叮咚。这时,也是牦牛产奶最多、质量最好的时候。最好的奶牛在这三个月每天能产六七斤奶。藏族女性蹲在母牛身侧挤奶的场景,成为了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素材。这时候,女人们的辛劳也带着一种富足的光芒。天刚破晓,她们就挤过了头道奶,然后,男人们将牦牛放出去吃草。中午,牛群就被赶回来,休息片刻,以便再次挤奶。挤完奶后,牛群再次放牧于青绿草原,直到太阳落山前赶回。趁着暮色还没有完全铺向大地,女人们第三次拎来木桶挤奶。天气暖和,牛羊放牧时间长,羔犊正在长大、上膘,畜群安闲,间或发出的声息也带有着一种满足和适意。帐篷里的灯火亮了起来,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坐在散发热气的茶饮前,享受草原美好的时光。
从驮运行走到贡献牛奶、牛毛牛绒,再到牛肉牛骨牛血,牦牛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人类。风干牦牛肉,是牧人家家必备的食品。干硬、有些刺嗓的牦牛肉干,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营养,给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付出巨大体力的人们提供了能量。牦牛粪一样是草原上的宝贵东西。对于半游牧和采取季节性游牧的人们来说,牦牛粪不仅是燃料,同时也是绿色环保的保温材料。在他们的冬季草场定居点,我们通常会看到土坯房和用于御风保暖的牛粪圈。
时至今日,大规模蓄养牦牛已经成为藏区提高经济水平的一种方式。牦牛绒光泽柔和,弹性强,手感滑糯,比羊毛更加保暖柔和,近几年已经被应用于服装生产领域,成为继羊绒之后又一种高档纺织原料。医药公司以牦牛皮为原料研制开发的牦犀胶,在市场上颇受欢迎。牦牛骨髓自古就被人们视为补品和药品,在壮骨强身方面作用明显。至于牦牛肉,就更不用说了。牦牛鲜肉和其他类型的肉产品,越来越受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
青海是牦牛大省,被称作牦牛之家恰如其分。根据年青海年鉴记载,青海牦牛主要分布在青南牧区。从年末存栏数看,全省牛存栏数约为万头,其中90%为牦牛。其中,玉树藏族自治州约为.6万头,果洛藏族自治州为82.5万头,海南藏族自治州为63.5万头,黄南藏族自治州为51.7万头,海北藏族自治州为50.7万头。
牦牛具有极强的耐力、耐寒力,牛乳、牛肉、牛毛、牛粪都是一代代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随着游牧、放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牦牛开发的一系列产品,成为青藏高原对外特色经济的重要链环。集群或圈养应该是牦牛品种退化的原因之一。据《西海都市报》年12月27日题为《青海省已有3处国家认定牦牛资源》一文报道:自年起,大通种牛场和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所、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及青海省畜牧总站全面开展了牦牛新品种培育工作,并连续被列为农业部重点项目。经过20余年的不懈努力,年利用野牦牛为父本培育的产肉性能、繁殖性能、抗逆性能高于家牦牛的遗传性能稳定的牦牛新品种诞生了,它是以我国独特遗传资源为基础,依靠自己独创技术培育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牦牛新品种,新品种的成功培育填补了世界牦牛育种史上的空白。该品种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培育的牦牛品种,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牦牛育种史上的空白。
长久专注的科学实验取得了良好效果。报道说,近日,由青海省农牧厅申请,青海省畜牧总站负责申报的“环湖牦牛”“雪多牦牛”两处牦牛畜禽遗传资源,顺利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正式成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并列入名录。至此,青海省通过野牦牛、家牦牛改良培育出的国家认定的牦牛遗传资源达到3处,分别是“大通牦牛”“环湖牦牛”和“雪多牦牛”。
野牦牛的种群正在增加,家养牦牛的体质正在增强。作为世界牦牛之都,青海向世界展示了另一种与众不同的形象。
推荐阅读
●果洛课间舞蹈操录制完成全网首发
●?????????????????????????????????
●????????????????????????????????
●马盛德:人们最终会热爱自己的文化
●格萨尔文化:果洛旅游有了“魂”
●传承人不仅是昨天的守护者,也是当下的主人
文字丨西海都市报
图片丨肖巴、网络资料
编辑丨恰嘎·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