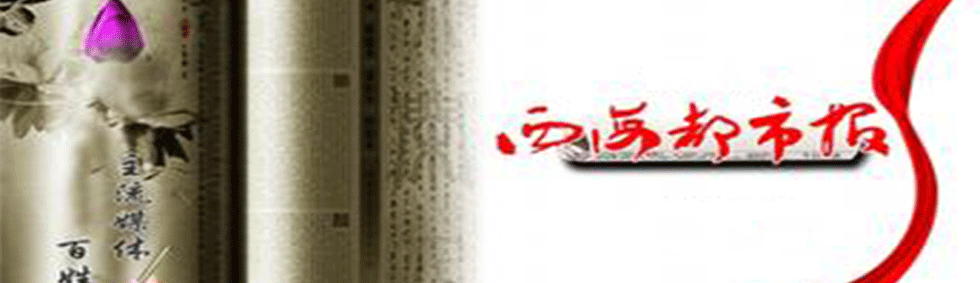
我的故乡,一个山洼洼里的小村子。那里,没有江南水乡那么繁多的果园,但盛产的水果却不少哩。有桃子、杏子、李子、秋子、冬果、苹果梨……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缀满枝头的香喷喷的沙果。
我们村叫沙果村,这名儿虽然有些难听。可每逢农历七月前后,村子里远远近近那数不清的沙果树上就挂满了红红的沙果。微风吹来,老远老远就能闻到那浓郁的香味。打我记事时起,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些沙果树。我家大门旁边那棵一人围抱不过来的沙果树,听奶奶说,是我爷爷年轻时栽的。它每年都会给我家添进几百元的收入呢!
幼年时的我,每逢和奶奶一块嚼沙果干的时候,奶奶便会对我说:沙果好吃树难栽。老树到了不结果的时候就要砍枝。还要把树窝子用土埂围起来。等来年老树的根须上长出嫩枝枝,过三年后才能嫁接。吃沙果,要在嫁接后再等三年。到了秋季,沙果树要剪枝、施肥,还要在树根旁挖个大深坑,灌水泡透根根。冬季,又要刮树皮,为的是冻死树上的害虫。
村子里的沙果树,谁家栽的谁家管理,收果也归自家所有。然而,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一场“共产”风刮来,大大小小的沙果树都变成了集体领导,平均分配的产物。又过了一阵,也不知是谁的发现:旱山头上造田好。负责人一声令下,村子里男女老幼都被动员起来,几天时间,花果山上那五六百株沙果树,便被砍了个精光,就连树根也未能幸免,许许多多沙果树全部送进了公社大食堂的灶膛里……
渐渐地,吃沙果的人多了,而务劳沙果树的人缺少,沙果树也不像过去那么添还人了。以前外地人曾说:沙果村的沙果鸡蛋大。但那个年月,沙果村的沙果变得像鸽子蛋一样小了。我家大门旁的那一棵,由于我奶奶娘家的成份是大地主,丝毫没有务劳沙果树的权利,也像别的沙果树一样,大多是些枝丫,而很少结果。一时间,乡村没了笑语,没了欢声……
屈指算来,我离开故乡,整整十多个春秋了。家里常来信说,村里早已大变样了,家家户户富得要冒油。很想回故乡看一看,却一直未能如愿。可每年沙果成熟的季节,我都会按时收到亲人们带来的又大又甜的沙果。每当这时,妻子总要唠唠叨叨地数落个不停,说嫁给沙果村的人,却未能去沙果村一饱眼福。我对妻子已许下诺言:今年沙果成熟的时节回故乡。我想:回故乡后,要和童年时的伙伴们聊三天三夜。更重要的是要给十多年前长眠在那里的奶奶,祭献上几碟香喷喷的沙果,给奶奶报去一个新的讯息,新的向往……
.2.20《耕耘》
作者简介:阴汉武
男,青海乐都人,年出生,年开始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曾仼青海《海东时报》记者、编辑,广告部主任。《西海都市报》驻海东记者站第一任站长。现退休。新闻作品40余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工作中始终恪守:记者就要坚持党性原则,敢于揭露违法乱纪的问题和各种不正之风。其采写的许多批评性新闻作品(包括内参),先后受到原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宦爵才郎和中共海东地委(市委)书记刘耀的充分肯定和称赞,赢得了群众的欢迎。创作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现居四川成都金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