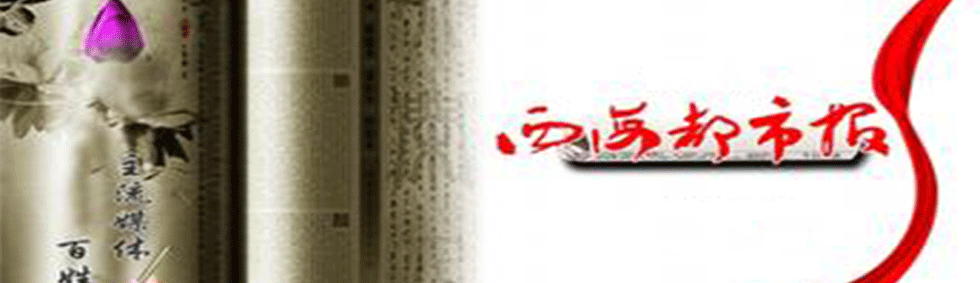
����ʮ������Զ����
��������˵�����غ����ӹ��硰����ʮ��������
�ģ�ͼ�����
��С�����˷�ϸϸ�������������������µĺ��ң��Ͳ�������ĵ��������¿��˻�����֮����˷��ġ������ᡱ�����ᣬʹ�ļ��ĺ��ұ��һ�����ϡ�
���������ɴ塱���ޣ�Ϸ��̨�����������߽����Ҵ�ׯ�����۴�ˮ����������dzɽ��ɽ��ׯ������������Ϸ̨����Ҳ������䡰����Ե�ʡ��Թ����������ҹȵ�����һֱ�ѡ����úܸ߹�������ƣ���biangbiang��ˣ�����Χ���š��������У�������Ů���٣����ԡ����š����š����ţ����š�����˭�Ҷ���Զ����˭�Ҷ��ܽ����븻��ƽ��������������̵�ѪԵ��ϵ����ľ���������Զ�����Ի��ġ�
���ں��ҹȵأ��������������غ����ӹ���ġ�����ʮ�������ᣨҲ��֮Ϊ���ʽ����ᣩ���ں��ҹȵ����ڵ��������������ա���硢���꣬��̨�µ����ӣ�����������֡�����������룬����һ�������ζ����
һ
˵�����غ����ӹ���ġ�����ʮ�������ᣬ���ຣ��ԭһ������Ӱ�죬����ֻ��һ�����������ӣ����Ǻ����Ļ���չ��һ��������л�����⣬ʢ���ں��ҹȵأ�Ҳʢ���ں����������ǵ����С������������������ˣ��������£�����ʮ�����Ϊ�����̷������Ρ�
������ʮ������ԴԶ�������Ծ���������Ǻ����ӹ���Ĵ�ͳ���ᣬʱ����������˵���ũ������ʮ��������������˵��һ���Ǽ���ع�����ү���������ӵģ�Ҳ����˵����ʮ���ǹص۵�������ĥ�������ӵġ����صۣ�������ʱ���������Ƴ����Ӷ����ݽ�ɽ��ʡ�˳��ˡ�������ǰ����˫ȫ���������������ʱ�˾��ء�������ܱ�ɱ�����¼�ͨ��������־������������־����ʷ��������������������һ��˵������������ʮ�������¡�ĥ���ꡱ֮���ء�
˵��ĥ���ꡱ����������ִ�˵��һ��������ʮ����ն���������ӣ�ĥ�����ն����������һ��˵����������ᣬ���ھ�δĥ�������ڶ����ˣ���ʱ������һ��ĥ���꣬����ү����ĥ����ݶ��顣ÿ��˵����ԨԴ������ʷ�����������ۺ��룬���ϲ������������ɫ֮״�������������Ժ�֮�С�
���Ƕ�˵������ʮ����ĥ����������ʮ����������ء�������ʱ������һƬ�����죬���������Ʋʣ���������¡¡����������¡¡�������������ǹصۻ���ĥ������������һ���µ��꣬ν֮������ʮ��ĥ���ꡱ�����첻��������꣬���Ƕ�������̨ǰ����Ӯ�ô�ҵ�һ�³ƺá��ڼ����У���������ʮ��������ļ��ʺܴ����绹��������ã������䲻����������������б�ꡣһ����һ��û���꣬��������̾���������ɲ��á����ǻ�˵������������ʮ����������ʮ�����磬��������˳ûָ���ˡ������ǵ����ȣ��ڳ��ڵ��Ͷ������У���Ȼ�����������ǧ�Ų����ũ�裬���һ��Ƿdz���Ч���ܲ��۷���
�����У�ÿ������ʮ���غ����ӹ��翴Ϸ����ǻ�������Ͳ�Ʈ�㡢�����ﻨ��ɫζ�У��ҳ�������һ�ַ�ʡ�������ѵ�������Ϸ̨��������ʱ��������Ҷ�����ĵ��Ȱ��ͶԹ�������ѵľ�����
����ʮ���������������״塢�̼Ҵ塢��կ������ˮ·����կ��վ�������Ϊ��կ���������ٰ졣�������£��ٰ�˻��ׯ�Ӵ����Է���Ǯ�������µ����°�����֮������ʮ����������Ļ�������ʻ��ʡ�������š������������һ������������ÿũ�����³����峿������������һ���������ģ�����ʢ��ı�������ƻ���峿�������������������������ʪ�����Ұ�У�ֻ��ɽͷ����Ʈ�����������ģ�����֮����ǡ�����ѳ�����ֻ��ɣ�������������������ף�����͡�
������ʽԤʾ���������ʽ��ʼ��ʮһ����ǰϷ̨�����嶼�д����Է��ィ����Ϸ̨���һ�ʵ����ɷ��裬��Ϊ׳�ۡ�����̨��ʮ��Ϊ�����ӣ�ʮ�������Ļ������Ϊ�����졣��������������ʮ��������ǻ��˧����Ա�Ժ���������ӹ��硢����ֱ���磩�����ġ�ƤЬ�ࡱ����Ϊ���������ӹ��������ֱ������ɵ���ǻ���ſ�νԶ���������������ҡ����ݳ���װ�Ƚϼ�ª��ѥ�ӵ����Լ��͵�ȡ�ķ��ƣ����������׳�Ϊ��ƤЬ�ࡱ����
���⣬ƤӰ�ӡ�ü�������ຣ������¶���Ӱ�Ʋ�����������������ľ���Ԫ�أ������Ŷ�Ԫ�ĺ����Ļ��������������ũ�彨������չ��ũ������ˮƽ�IJ�����ߣ�Ⱥ���Է��齨���С�����ţ����������ʹ����ʮ��ɢ��ŨŨ���Ļ���Ϣ��
ÿ������ʮ�����ᣬϷ��������ž������������˷�����������ũ�ŵ�ѧ�ӡ�С�гɾ͵���ʿ���������λ�����֮��ÿÿ����ǰ�����أ�ֻ�������������������洺�磬�˿̣�̨��һƬ������̾����Ϊ��ĸ����������ѣ����Լ��˺��ѳ���ͷ�ض��Ժ���
�������������ʮ����ʷ�ƾã�����Զ������������Զ�������ڣ��������˺����������ܱߵ������̼����˳�����Ʒ������Ҳ���������������һչ��ɡ��������ƣ�����ʮ����չ�ɺ����ӹ���Ĵ��ʹ�ͳ�����Ļ������ᡣ
��
���������������ӹ���ġ�����ʮ�������ᴿ����һ����������Է���ӭ�������������ũ�������IJ������ص۹���ү�йأ�����������ӭ����������ݵ�����ʱ�ڣ���ũ���ڴ���������������ն����еļ�������������ׯ��ϲ�������ʹ���ֺ͡��еġ�������������ģ�֪��������绹��������½�Ρ�����ʫ�塷�еġ����Ҹ�Լ����Ů�����պ��ſ�������ָ���ס�
ÿ�����ᣬϷ������·��С������ߡ�����һƬ���֡����ν�ǣ������ﻨ�����죬��ǻǣͷ֯���ꡣʱ�����³��߰ˣ�С�������������Ƽ��᳡��������ռ���̣�һ����Ϸ̨���������Ѵ�����ǻ�Ŀ�����׳����֮�����ij����ȡ�ÿ����ʱ������������У���飬����ǻ�����ɽ����ǣ�ߣ��μ���һƬ������ס���е��궯����ν�����ڲ�Ӫ���ں�������ѧУ��һ��������ͷź���������ȶ���
����Ϸ̨����Ϸ�������ı�ƽ�����Ļ����ž����ˣ��¸��̸踳����������ʮ��һ���磬�����������������ܱߵ�������Ů����,���Ž���ʢװ��������˷�������ӹ�ӿ��,��·С��������ɽ�˺�����ɡ��䡣����ʮ�������������������������尢�ø��ǻ᳡��һ�������ķ羰�ߡ���һ��᳡����������£����尢�������Ž����߲������ձñ�ϲ�������̺�ľ�������ɫ˿��������ʰ�쵣���֮�����������ϸ�Ĵ���ͼ������������������ɡ��ӳ���£����߲ʵķ羰ʹ����ʮ�������˺�������Ļ��ĵ��ں���
Ϸ̨��������������죬ʱ���������գ�������Ȼ��
Ϸ̨ǰ��ͷ�ܶ�����ѹѹһƬ����ͷ��̫̫���Ϸ������ʯͷ�����������ϣ���Щ�ɴ�ϯ�ض�����С���Ǽ��켷������������ǻ��Ҳ��̨֪�ϵ����ڸ�ʲô��ҲҪһ����Ա��ɣ�ʵ�ڼ�����ȥ������ǽͷ����Ԯ����֦辣�ҲҪһ���۸�����������ֻ�����������̣���������̨�ϵ�������Ȧ�ӣ�ż���д������ݵ����ij�Ϸ��������Բ�۾�˵������������������ֻ��סһ��������ӣ�һ������������֪����Щ������ʲô���ȱȻ�������ǹ����������һ��Ȼ����������ͬ��������Ѫ����ա��������ն�й١����������ˮ�������ߴ�������һ������������Т����Ϸ�飬ʹ�����������У��������飬�����䣬��һ�����ܡ��������ף�Ҳ��ɢ��������ֿ����ǻ�����顣
���ž�������룬̨��̨�µľ���Ҳ�Ͳ�����ôңԶ����ƤЬ�ࡱ�ij����������㲻��¯���࣬ȴҲ�ѵõ��������á������Σ���һ�ζ�����ټٵġ���ʷ�������������DZ����������������ᣬ������ĸ�������ան���ĺ��ô�������кã�ˮ����ɽ�����ڰ��һ������ͬ��������������ķ�������ҵ���������£�����³Ѹ�ġ��������ĵ�����֮��ζ��
˵��ա�����������еij�������������״Ԫ���ֵ���������ԭ��������������Ů�뾩Ѱ�²��ϣ���ʹ�ҽ�����ɱ����ĸ����ڡ��ؿ�ʵ�飬�������������á��ص��������ظ棬������������������ض��ʡ�������Ϊ���ݣ�ǿ�ʽƱ硣����ա֮��̫�ʹ�ǰ��Ȱ�裬�����ˣ�ա����������
���ݡ�����־����ʿƪ������:��˳��ʮ���꣬��δ��ʷ��ɰ���ȣ��ٹ���˼ʯ���水��˾��ʹ����˾���������־ݡ�������ʷ����ǵ䡷����:�������������Ա��ԭ����ȣ���������������(���������أ��ֵ�������)�ˣ��������˹�֮�ҡ������ѧ������˳�ΰ���(��)��î�ƽ�ʿ�����κӱ�ij��֪�أ�����ÿ�����ʶ����Ϊ���ݷ���˼�ʸ���ʯ������ʹ���沼��ʹ�������ڹ���Ϊ��ʱ��ͬ��ͬѧ��Ͷ��ıȡ��ְ������νӴ�����Ȱ�Կ̿�������˽���������Ͷ���ն࣬����Ӧ���������ܹܼ�һ��л������ס���ݳǽ��ؼ��µ�ͬ�����ε�������������������ʱ������Ǯ�������������ܹܼһؾ�����������֮�ģ��콫�����һЩ���ٷ��ơ������������������֮�£�����һ�𣬼��������ϣ����Ϸ�硶���������������������ϵȵ��ݳ���
���ڳ�������ԩ�������ں�����Ĺ㷺����������Խ��Խ����������ѧ�ߺ��йز��ŵ��о������ӡ���һЩѧ�߶����о���֪������������ʷ��ʵȷ�����ˣ�������䴫˵�����ڵ������з��ֵ��йس������ı��ļ��أ�����������Ϊ����������ֱ����������������١���Щǿ���������ϵ���ν��ƶ������ɱ������֮�£���ϵ���Ͷ���֮����Ϊ��
���п��Կ�������ʷ��Ϸ������Ҫ��һ�㣬����Ϸ˵����䱼��أ������£���ǰ�̵���ͨ�ˣ���֪��������ʷ�е���������ģ�����֪�������࣬��һ���dz��ı���ũ�����˵ij�Ұ֮�ˡ�
������ʮ����Դ�Ժ�ʱ���������Dz��ö�֪�����ǵ���֪��������үү��үү��үүʱ�ڣ����С�����ʮ���������������ᡣ����ʱ�𣬺��ҹȵ�ũ��ļ��ϵ�������Ŀ��أ�һ���п�ȹ�������Ϸ�����֣���������Щ���룬���ۡ����ۡ����š����š����Ǽ���Ϸ̨�ϣ��ڳ��������У�������Ѫ����ա��������ն�й١����������ˮ�������ߴ�������һ����Ϸ���λε����ţ�һ�����������衢������Խ���ȶ����ĵġ���֮�������š�
�������껨���ƣ������������ͬ����Щ��������ľ籾�������þ�άϵ���л��Ļ���Ȼ�������ź��ҹȵء���ʱ�۹أ������ڲ��£���ʱ�³ǣ���ǣ����dz�������Զ��Ѱ�š���ެ��������䡱���㼣�������ź��Ҷ�Ůʥ�����ࡢ��ˡТ����������ң������ź��Ҷ�Ů��Ӧ��״���Ƿ�����
Ϸ��̨����������ʷ�������ŵ������ֻ࣬������̨�ϵ�������ſ��Ե������Ǹ߹��ͷ������䣬����̨Ҳ��������ٻ��⡢��������������������İ�����Ӳ���˺���
̨�Ͼ���ǧ�㾰�£����ַ��飬�ɾͺ����ӹ�����������������黳������ʮ��������������������ʷ�������ŵ������ࡣ���ᡢ��̨���籾����ʷ�еĵ���������䡢�߳ܣ������ġ�����ʮ�������ᣬ��õ�Ϸ̨���������ĺ�������ġ�ƤЬ�ࡱ���ˣ���һ������ļ�˽���һ����������������ϼ䣬��һ���������Խ�ij�ǻ�У������ˡ�����������������ĺ��������ȣ������Գ��һչ�۲Ŷ�������ʷ֮�ƾá�
��˵�����ӹ��粻�����صأ�������˹����˹�ĺ����ӹ������Թ�ֱ��˵��Ӳ����������Զ��ֻҪ����˵������֪�����˾��Ǻ����ӹ��ˡ���ԭ�����ں����ӹ���Ӳ���Ŀ��P��j��q��x��z��c��s����1��4��7�����ֵķ�����Ϊ�ˣ����Թ�ֱ��˵��Ӳ���ĺ����ӹ���ϲ���ľ��Ƿ������ء�ҧ�ֺܺݡ��������ұ�׳����ǻ˺���ѷΰ����ǻ����������������ʱ�������������ij�ǻ�볪�ʡ�����ƾ���ڳ�Ϊ���ˣ��к�������֪�ߡ����н���ȡ������ʨ��һ��Ԫ��ӡ��������һ�־��춯�صĸо���Ҳ�������ù��ڵĺȲʡ�
�����ڼ䣬�������������죬����������ǻ�Ӳ���ϣ�����һ�ɡ��˰����ش��Ƴ������ǧ���������ǻ��֮��ζ���ǽ���ȫ������������Խ�ij�ǻ���˴��롰�����ɽ���²�������Ѫ�ס�����ϣ����롰��ɳ��ս����ײ���¥���ղ������ı�׳��Ҳ���롰�����Ʊ��˸�ĸ�顱���᳦��ת���������֮������������繡�
���ܣ��������������ƤЬ�ࡱ����Ա�ǽ���ǻ���������صط�ɣ���ȱ��רҵ��Ա����ǻԲ֮�ص�������ˣ���һ�����д�ͳ��ζ�ľ�Ŀ��Ϸ���ǰ������ᣬ����������
�����꣬������ǧ�����������ӹ��磨��Ϊ���壬���ഫ�������Ͼ�����������֡������Ļ����Ͻ�������������ͳ�Ļ������½���ظ�ԭ���������ź����ӹ��ĵ�ϼ��ò�����ź����ӹ��˹�ֱ�ĸ�����Ӳ���Ŀ�������Ͼ���������Ĵ�˵�����ź����ӹ��Ļ�����Ľ������ɳ�����չ�����γ��������������ѡ�����������Ļ����������ӹ�������Ļ��ġ�С��ͳ����Ҳ��������˺����ӹ�������ϲ���ּ��ġ�����ʮ����֮�����Ļ�����̬�����淶����һ��ˮ���������ź����ӹ��˵�����뾫��
������ʮ��֮ʮ�������ʱ�䣬һ���죬���������Ϸ̨�϶����������ࡢ�ġ����������ҡ����ŵȸ������������������̨�ϵġ����������ɡ������ּ������ĵ�������Ʈ������ʪ�Ŀ����У������������˵����ϣ�ʹ���ޱ���ů����Ϸ̨�ϵġ����������ɡ��������ʷ����������ʷ��Ҳ�����˺������ڵľ��������룬�Լ����������ڽ����涨���ֵĵĻ�ë����̨����ͷ�ܶ�����һ������������������Ϸ̨�ϣ�������ĩ����������һ������ɣ���µ�������Ϸ�������Ǹ�����������ϲŭ���֣��������١�������Ѫ����ա�������Ⱦ����е��Ƕε���ǻ������������ۡ����úð�������ʱ��Ϸ�����ݳ������ˣ�������Ա�ij������������ɾ���������ս������
��
����ʱ���ı�Ǩ�������Ļ�֮�������ӹ���ġ�����ʮ�������֡����Ļ�����̬Ҳ�������������ں�����ϲ���ּ����ִ����Ҳ������̨����ʹϷ����ͷ�ܶ����������ס�
�����ӹ��ġ�����ʮ�������������꣬����չ���������ص��Ļ����ϣ������Ź��ϵ��Ļ���Ϣ��Ϊ����˹����˹�ĺ����ӹ������ڴ�����������Ȥ����Ϊ���DZ����Ļ�������������Ե���Ҫ�����������Ŵ˵ص����ڿ��������֡�
�����ʮһ���ͣ���������彨�������У����ҹȵصġ��塱��ׯ����̽�����Ϸ̨������˳¾ɵ�Ϸ̨���������ӱ���̡����ǣ�Ϸ̨��Ϊ���塱��ׯ�����ֵ����ģ���ƽ��ƽ��֮��ϵ��������˺���ѷΡ������Ҷǵ����顣���Ļ����硱�����ᡱ���Ϊ��������ζ�����������£������ˡ�����ʮ�����������߳������ӹ����������ӵ���Ҳ�Ϳ�ʼ��ǻ�������۵������졣
��г�������ƾ��ó�Ϸ���¸�·�������Ļ���̨��
ÿ���ũ������ʮ�������ó�Ϸ���Ļ���̨����������˳����ȷ�ǡ�������ʮ������Ϊ��ͳ�Ļ�����˵������Է����������������ӹ��絳ί�����ӣ�Ϊ��ʹ����ʮ���������ִ���Ϣ���������ڴ�ͳ�Ļ��Ļ����ϣ�����ʡ�����������������Ļ����磬����Ⱥ����������Ⱥ�ڴ���һ�������ִ���Ϣ�ĵ��Ļ���͡�
����ʮ��������ũ��ĺ�г���磬�ٴθ��贫ͳ�Ļ����������ں����Ͳ˻����Ʈ�㣬����ӭ�����룬Ϸ����ɡ��䣬С��ߺ�ȴ���˷����ֿ����ǻ��������ת���ຣ����������������ִ�����Ļ�����չ���ź��Ҵ�ͳ�Ļ��ķ�ɣ���д�ź����������������ĵش���������ϼ��һɫ����ʫ�⡣
Ϸ̨��Χ�������۵ģ�������ġ�������Ƥ�ġ��������ǵġ�����������ȥ���ˣ�ʲô�����ѡ�ѩ�⡢��ը���㶼�У���Щ�������˲���������������������ֳ������������䳾�������˿��Ҳ�赲�������ǵ����顣
��·�ϸ���Ħ����࣬·���ߵķ���Ʈ����Ũ���ຣũ�ҷ�ζ���˵��������ຣ����Ƭ����Ƥ�������������ο��Ǵڸ����������������ں���ߺ�����Ʊ���յ���ȵ������ࡣ������Ŀ����Ʒ�������ο���פ��ۿ�����ˮǹ��С��߸������˺��ӵ��������䰮�����֡�
Զ��᳡�ĺӱߡ����ֳ�Ϊ���������ߵ�����˵�����������顢Ұ��¶֮�ص㣬����һֱ������ɽҰ������С���ϡ���ؼ䡢ɭ���������������������ϣ���ȥʱ�����������ׯ�����ȥ����³����㳪ʱ�Ϻ�����������ƽ�գ����������Ǵ����ڴ��Ӽɻ��Ұ�����Dz��˴���֮�á�Ʃ�磬���Ȼ��IJ�ñʮ��ת�����Ϲ������ģ���ά�Ļ����Ǵ��꣨�ຣ���Զ�����gou��������§�Ϲ����Ҷ��ġ������ع����������ǹ����ػ���û�У�����ҧ����Ҫά��ά�����ϰ�磨�ຣ���Զ�����za�����������˳�ƨ�����������ԣ��������������Ž����ҹ�ִ�������ຣ����ʱ�������ຣ������Ҳ�ơ����ꡱ������Ԣ��ֱɣ�Ω��ƫ����Ů֮�顱�����ຣȥ������
Ψ������һ�죬�������������������Ⱥ�������������ϡ��﹡�����֡��ݵؽ��ǻ�������̨�������ľ��̷ʺ��ݵ����ֱ��һ�����졣
���ߣ�����������ʮ���ߡ����������˻������ߡ������ǣ����ˡ��᳡������������Ϊһ��������һ�����������ˡ�Ҳ�ͳ�Ϊ����������֮���һ����������ϵ��ʽ����������Ȼ֮���һ�ִ�ɺ�Ĭ����
�����һ�ӷ���ȥ�����Ż���������������ˮ��������ľŨ�����˻����磬������裬һ���������������������������顣�����Ⱥ������������С��ģ�Ļ������ֳ�Ϊ������ʮ����һ�������ķ羰�ߡ���
�����������С���ã����ү����������������û�����ij������ij�����������������ȸ���䵽��ʯ�壬����������ĺ����������᳡����һȦ��û֪�����������䡣��������ɽ��������������үɽ�������������Ҽ��˻�����ͷ̧����������ɵ�������������һ��������������������ѵ��ຣ�������Ǻ���С�ٿƵ����ԣ��������ͽ��֮���ӷ�ɡ�ϯ�ض����ĸ��������°ͣ���Ů�Գ��������������䣬�Գ��߳�������֮�����Ȳ��������������Ͽգ����Գ��ߴ�������ʱҲ�Ի�������ʧ�ܣ������ϵ��������µĻ������Ѹ���ץס�ˣ�Ҫ���˳��ϸ���Ϸ�������������ס�ˡ�����������Χ�����Ϲ�����һ�أ�������������ݵ��ϡ�С���ϣ�Ũ���£��﹡�ߣ�����һȺ���߰�һ��ظ����裬�������ڣ������ֳ������Ļ���Ũ�����ֳ��ȳ���ͳ�������ڵ��Ļ���ᣬ����һ�֡��ŵ���������������������ʱũ���ִ�������ĪЦ�����ʫ�黭�⡣
С�ӱߡ��﹡�ϡ��Ͳ˻��£���������������磬С�����̸��˵�����������ҡ��������գ������ﻨ����һ·����ӯ�ƣ�һƬ��Ͱ�����һ��ݺ���������ʮ����Ҳ�ɾ��˶��������Ů����������֮Ե�������������Ӹ�ĸ֮��������ý��֮�ԣ����Ҳ�б���ĸ����������һЩ���ۣ����Dz��۶��������ģ���������ʮ���������һ����ѻ��������������˲��ٵĻ��롣
�����������ö�����ҹϷ������Ҳ��һ����Ȥ�������貵ƻ𣬵���Ȼ��ɽ�˺���Ϸ̨�Ϻ������죬����ƤӰϷ��֮��������Ӱ��¼�����С������Ļ����ͷš�ֱ���������죬ҹϷ�ճ�������ɢ�������ֵ�ϲ����
����ʮ��������̰��������°���������һ���Ļ��ķ��Ҳ������ũ�徭�÷��١���ǿũ����Ʒ��ͨ��ʢ�������Ļ������ᡣ����ũ�����������룬������Ũ������䴫ͳ����������棬�������ĵ��黨���ᣬ���°˵������¹ؾ��ᡭ���ḻ�����ǵľ������Ũ�����Ļ���Χ�Dzʺ�Ĺ����ٶȴ��조�캱���ɹš��ĸ�����
������ѩ�ѽ�ȥ�����������ﻨʱ��Ը���������ʮ���ڲʺ�֮����ڷ���������ʱ���Ļ��¡�
����
��������ຣ�����ˣ���Ϊ�ຣʡ����Э���Ա���й���Էɢ����ǩԼ���ң��й���Ȥ��ͨѶԱ����ʮƪ����ͨѶ�����ű�����ɢ��ʫ�ʷ����ڡ��ຣ�ձ�������Դ���������������б����ȱ�����־����ƪɢ����ʡ�������ı����л��ֹ�ְ�������н���ϵͳ���ຣ�����Ļ���ýǩԼ���ߡ�
==============================
�ຣ�����Ļ���ý��Ʒ��ԭ����Ʒ������ת�ء����ຣ���顷天津市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表皮转移因子胶囊能不能治好白癜风
ת����ע����ַ:http://www.wangxingxing.net/xhdsbfz/5956.html